头顶上像是开了个无形的天窗。以前只能盯着脚前巴掌大的地方,现在好了,目光能往上飘,能往远处溜。灰蒙蒙的天空,远处起伏的山脊线,甚至那些躲在高高石柱子顶上的、闪着贼光的小玩意儿,都清清楚楚。更绝的是,连地上哪儿藏着条不起眼的缝,哪片草皮底下颜色深点像是能挖,都跟画了圈似的标出来。这哪是斗笠,简直是开了透视挂。
走路都不看道了,光仰着脖子扫视天上地下。好东西尽往高处藏?以前爬不上去干瞪眼,现在踩着几块破石头就能轻松够着。角落里有矿脉闪光?以前钻进去十次迷路八次,现在隔着老远就瞅准位置,两点一线,省下多少瞎转悠的功夫。效率高了不是一星半点,包里鼓囊囊的,全是以前不敢想的好货。这斗笠,真他娘的是个宝贝疙瘩。那破斗笠扔角落吃灰不知多久了,篾条都散了架。那天被野地里的毒日头晒得实在没招,顺手就给扣脑袋上了。奇了怪了,沉甸甸的破玩意儿一挨头皮,眼前唰地一下,整个世界都不同了。可渐渐地,有点不对味了。习惯了这俯瞰一切的神仙视角,脚下的路反倒模糊了。心思全在远处那点闪光上,脚底板踩到什么,硌不硌脚,滑不滑溜,好像都无所谓了。反正天窗开着呢,前方有啥好东西,看得真真儿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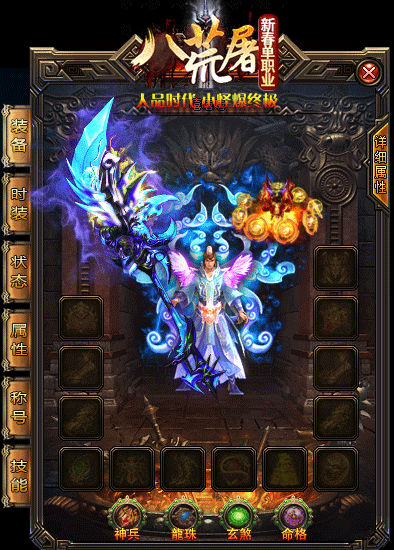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追着天边一抹贼亮的绿光跑,满脑子都是又捡着大漏了。脚下是片乱石滩,坑洼不平,搁以前走这种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。现在?心思早飞那绿光上去了。跑得正欢,脚下一空,身子猛地一沉。低头都来不及,整个人就跟块石头似的往下砸。耳边是碎石哗啦啦滚落的声音。摔得七荤八素,眼前金星乱冒。挣扎着爬起来,浑身骨头跟散了架似的疼。抬头一瞅,心凉了半截。掉进个深坑里,四壁溜滑,头顶那个曾经开阔无比的“天窗”,此刻只剩下小小一块灰蒙蒙的天。那抹勾人的绿光?早不知在哪个方向了。更糟的是,坑底弥漫着一股子淡淡的甜腥气,闻着就让人脑仁发晕。脚边几块不起眼的暗红色苔藓,正丝丝缕缕地冒着几乎看不见的雾气。刚才摔下来时,胳膊肘正好蹭过一片。被蹭到的地方火辣辣地疼,皮肤眼见着就红了一片,鼓起几个小水泡。这鬼地方,真正的杀机原来埋在脚底下。
使劲往上蹦,指甲在滑溜的石壁上抠得生疼,只留下几道白印子。那顶沉甸甸的黄金斗笠还牢牢扣在头上,视野依旧“开阔”——能看到坑口那一小片绝望的天,能看到坑壁上每一道无用的纹路。唯独看不到一条能爬上去的生路,也闻不到那甜腥雾气正无声地侵蚀皮肉。它让你看清了整个世界,却偏偏弄瞎了你看清脚下陷阱的眼。这金灿灿的斗笠下,所谓的清晰,原来是一种更深的迷眼。
